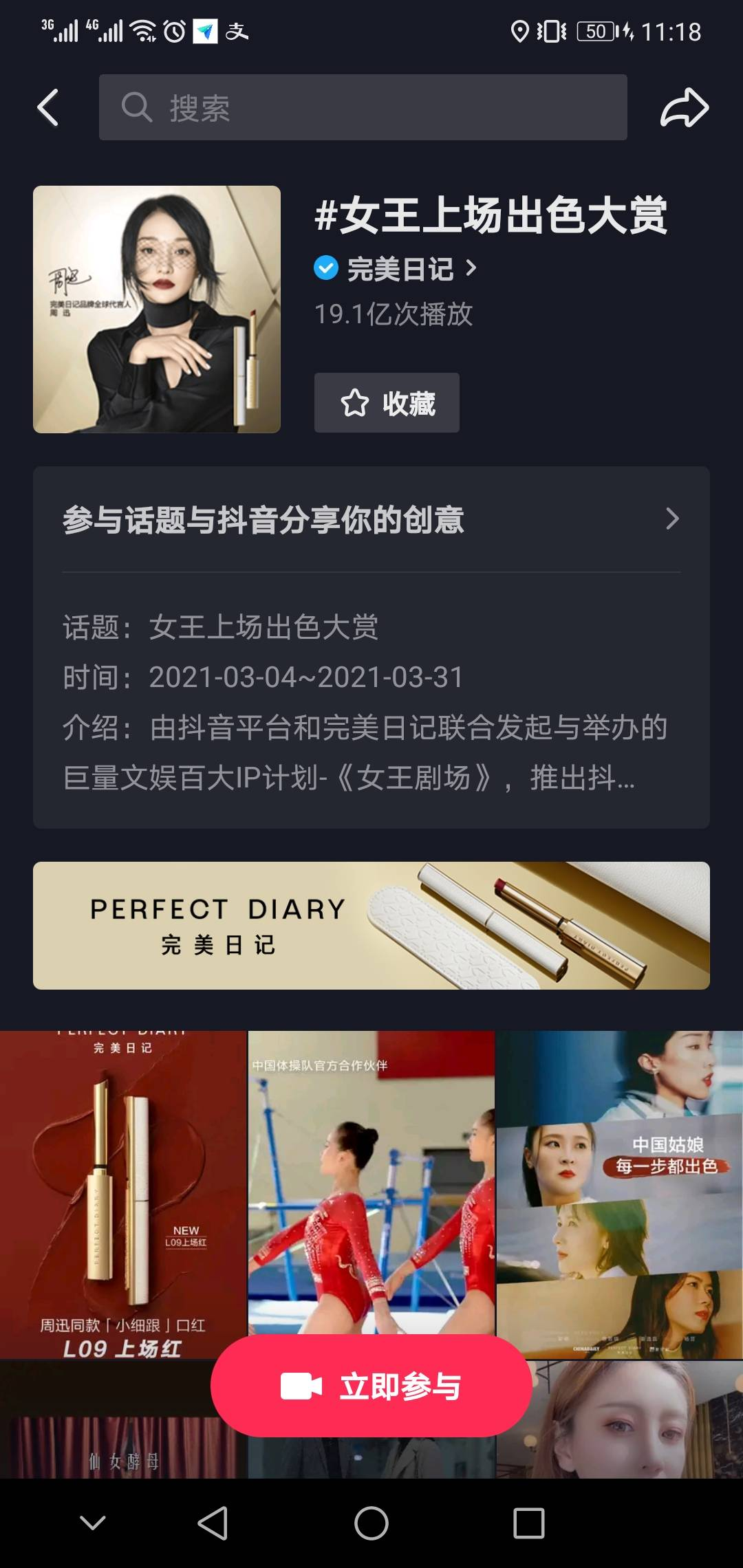《子夜》小说「雪中悍刀行是玄幻小说吗」
东晋子夕,
百鬼夜行,
这是最后一个人鬼并行的年代。
1第一场冬雪来了。
我挑旺了炉火,和武罗玩六博。一连五局,我回回得胜,武罗气得耍赖,一抬手,将棋子纷纷振落。
我不同她一般见识,走到门口看天色。北风卷地,吹得门前的琉璃灯摇曳不定。方才还只是溟濛璇花,怎料这会儿越下越大,转眼间已是台如重璧,逵似连璐。
飞雪中隐隐绰绰走来个人影,不待我定睛一瞧,那人影愈发近了,却正是阿姐,我连忙朝她挥了挥手,回头招呼武罗将火生得更旺些,又将风中的飘灯取下,一并带回屋中。
天地玄寂,我们三人无事可做,倒是阿姐先开口:“不如每人说个故事听听罢。”
如此自然是好,可该谁先说呢?倒不如以掷彩来决定次序。
就这样,武罗运气差,掷出的数最小,便由她先说。小狸奴蜷在火炉边,优哉游哉地讲起来。
第一个故事,是关于长命缕的故事。
2山洪卷着泥石飞流而下,龙景云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,再醒来时,只见天日高悬,晃得眼睛一阵晕眩,强忍着剧烈的头疼站起身,唯见石崩山裂,将好好的栈道全部掩埋。
这还不算,整个商队都被埋在废墟下,看样子,他是一队人中唯一生还的了。
来不及心疼价值连城的货物,龙景云唯有庆幸自己劫后余生。可独在深山,现下实在是进退维谷。
四下茫然间,眼见一白衣少年驱牛车而至,他连忙牵动嘶哑的嗓音大喊起来:“少郎君,少郎君,停一停!”
那少年闻声,赶着牛车走近,一看满目疮痍的前路,便什么都明白了。五月恶月,遇上这样的事,果真是应了诸事不吉的预兆。
龙景云向少年道明了缘由,忍着浑身上下的痛楚问:“郎君可是要去往江陵?不知可否载在下一程?”
“巧了,我正是要去呢,只是前路阻断,唯有绕道夔村方可。”少年笑嘻嘻地应。他面貌平凡,脸上却总带着笑,看久了就让人不禁疑惑,他到底在笑些什么。
听到夔村二字,龙景云犹豫了:“夔村荒僻,道路崎岖,且民风刁蛮,阳虚阴盛,不是个好去处!”
“如此,可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”白衣少年笑着扬起鞭,临走前还慢悠悠地说,“若是沿原路走回去,只怕要有几天的脚程。”
“郎君且慢!”犹豫片刻,龙景云还是绕到牛车前,阻住了少年的前行。
“改变主意了?”
龙景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。少年笑着扶他上了车。龙景云有些狐疑——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?
少年拍了拍拉车的白牛:“阿傍阿傍,启程了。”白牛听话地迈开步子,不多时,就转上另一条道。
途中,龙景云问少年的名字。少年答:“我姓谢。叫我小谢便是。”当然,他依旧是微笑着的,就好像只有这一种表情。
龙景云不知该说什么了,气氛变得尴尬,山野四寂,黄云垂覆,让人心都兀得忐忑起来。
猛然间,一个黑影自枯枝上扑下,带着凄厉的悲鸣迎面而来。
龙景云吓得向后一缩,那黑影却在离他不到三尺的地方骤然拔高,飞掠开去。
他这才看清那是只大鸟。此鸟鸣声极悲,比那啼血杜宇愈显哀怛,恨不能声声都剜到心里,渗出血来。
“咦?这是什么鸟?”小谢朝着大鸟飞去的方向远远眺望。
“荆山山民称此为楚魂鸟。昔年楚怀王崩于秦,魂化为鸟,是为楚魂鸟,楚国卿相遂为其招魂。还有一种说法是,楚魂鸟会带走生人的灵魂,每逢这种鸟出现,就会有一个人死去。”龙景云稳了稳心绪,却见小谢饶有兴趣地听着,他只得干笑两声,“荆地怪谈,郎君也信吗?”
“龙兄不信‘招魂’一说?”小谢却反问。
龙景云的面色微微一变,如锈蚀的铁器,呈现出冷而苦的色泽:“郎君大概不知荆地的风俗吧?就拿夔村来说,此处地处荆山,山高路远,还留有些巫觋之道。”
小谢连连点头:“哦?不知村中是否有灵巫得以让在下求访?”
龙景云闻言大惊,迟疑片刻则连声相劝:“哪里有灵巫,只怕是些妖邪。”
见小谢不信,龙景云又连忙说:“郎君有所不知,我在外行商常走这条道,也常听人提起那夔村的事。”
“哦?说来听听。”小谢似乎对夔村的事格外专注。
龙景云苦笑着拢了拢袖子,心想反正闲来无事,说些山野奇谈解闷似也无妨,最好能让小谢远远避开那个恐怖的村子:“我看谢君不是本地人,但在楚地,说起荆山,人人都知是个了不得的地方。”
小谢更是兴致勃勃:“此话怎讲?”
“在多年以前,夔村有个名叫蕙娘的女子。她是荆山下的南乡人,家中也是小富安康,却因为出生时克死母亲,十三岁时父亲又死于非命,因而被认定是身负恶鬼凶煞的女子,再加上是家中的庶女,不被主母待见,遂被嫁到夔村给一个名叫陈洛的庙祝当媳妇,说是唯有如此才能镇压恶煞。蕙娘过门没多久就生下一个儿子,名叫阿蓬。”
小谢聚精会神地听着,仍不作声,龙景云继续讲:“可就在阿蓬三岁时,陈洛也离奇丧生。一些虔诚保守的村民因此认为,是这个女人身负恶煞,激怒了神庙中沉睡已久的高丘神。所谓高丘,是荆楚先民对于山神的称谓。后来,阿蓬开始不断遭到鬼怪的袭击,据说那鬼以鸟的形状飞来,化为一团影子,意图夺取他的身体。再后来,阿蓬也失踪了,老人们又说是高丘神带走了这个孩子。不过从那之后,村子里倒是平静下来,大概是高丘神得到了祭品,驱散了蕙娘身上的恶煞吧。”
二人沿着山路前行,然而山间气候多变,故事还没讲完,方才还是白日高照的晴空,此刻又云如泼墨,风低万竹。
3之前下过雨的山路本就湿滑难走,眼看又一场大雨将至,龙景云再无心思谈笑,只盼望着早些看到人家,能够落个脚。听着滚滚雷声由远及近,龙景云心底刚道了句“不好”,山中已是大雨如注。
透过密集的雨线,前面的山头上隐隐静立着一座小屋,龙景云不由大喜过望,连拍了拍小谢的肩膀,将那小屋指给他看。
小谢会意,驱着牛车向山头走去,等走得近了,二人顾不上行动缓慢的白牛,一前一后地跳下车,连奔带跑地冲去。
待飞奔至门前,龙景云突然站住了脚跟,那破败的小屋并不是什么人家,而是荆楚之地常见的神祠结构。
“愣着做什么,快进去啊!”小谢抹了把脸上的雨水,推着他进了门。龙景云无意间瞥见,满脸的雨水将小谢的神情模糊成一个不明意味的笑容——那不过是雨水的缘故,他这般说服自己。
屋内破败的泥墙摇摇欲坠,雨水滴滴答答地从破窗和茅草铺就的屋顶缝隙间泄落,屋内结着长长短短的五色缕。自打入赘了龙家,龙景云就再没有见过这般凄凉的光景。就在他出神之际,冷不防听到有人说:“看二位的打扮,该是过路的客商吧?”
在小屋内难得干燥的一块地上,生者一堆篝火,围绕着火苗,零散地坐了几个人,一个老者,一个猎户,一个女子,一个坐在最角落阴翳里的青年。
“我们正是要去往荆州,只是前路塌方,只能绕道夔村,却不想天降大雨,不得不叨扰几位了。”小谢笑道。
“好说好说,两位快坐吧。”那猎户打扮的年轻人爽朗一笑,朝一旁让了让,“你们要去夔村?我正是夔村人呢!”
“哦?真是巧了,待雨一停,我们又多了个人作伴。”小谢向龙景云道。
龙景云礼貌性地笑笑,算作回应。
“你们也去夔村?我也是哦。”一旁的女子抬起头,看了他们一眼。龙景云心中一震,他的头有些莫名得疼痛起来。眼前这个女人素着一张脸,面容虽有些憔悴,却偏有别样的风情,就像泥土中开出的白色的花。
猎户十分殷勤:“小娘子真是好胆色。不瞒你说,山中有很多野兽精怪,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,都不敢一个人走山路的。等雨停了,你便跟着我们走吧。”
那女子笑道:“哦?可我看几位不都是独自行路的吗?你们走得,我又为何走不得?”
猎户被她泼了冷水,又讪讪地问那老人:“不知这位老叔去往何处?”
那老者一身酒气,眼睛半抬不抬,醉醺醺道:“我……我也去……夔,夔村。去,看,看,看我女儿。”磕磕巴巴地说完,从怀中摸出个酒囊来,灌了两口酒,又打了个嗝。
“老丈这么大年纪还翻山越岭地去看闺女,想必是极疼爱这个女儿吧。”
“那,那是当然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,当,当然得放心上。”
“真是有缘,大家都是去夔村。这位阿兄该不会也去夔村?”女子向那个坐在角落中的青年道。
那青年眉目清秀,衣衫洁晰,是与这荒山格格不入的书卷气。他好像有意同这些人保持这距离,只简短地回答:“不。我回建平郡。”
“你们都去夔村,可听过夔村中流传的高丘神的故事?”年轻的猎户神秘地笑了笑,刻意加重了语气。
“怎么会没听过?那故事里的女人叫蕙娘,就是我妹子。”女子美目清丽,顾盼生姿。
“妹子?小娘子你说笑呢,蕙娘如今都五六十岁了,怎得你还如此年轻?”猎户只道是她说的玩笑话,也并不十分在意。
而一旁的龙景云微微一颤,身下的茅草发出突兀的声音。
“呵呵,那便是我姑姑吧,怎么叫都行,总之这事儿是我亲眼所见。”女子笑道,“只是出了那事之后,我们家就成了过街老鼠,没几年就衰败下去。”
猎户挠了挠头,很是疑惑:“我从没听过蕙娘在夔村有过亲眷,老人们都说她家是从山外迁来的,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亲戚?”
“你别忙着疑我,且听我讲的对不对。”那女子扬了扬眉,先前的颓郁好似都随着飞扬的神色隐退而去,“我记得那年正是盛夏,蕙娘一个人入山,直到深夜都没有回来。家里的人在山上找遍,也没能找到一点踪迹。于是村子里就有老人说,难不成是被狐狸掳去了?你知道那里过去有很多狐狸,日子久了成了精也没什么奇怪的。可是,竟真的在狐狸洞里找到了蕙娘。说来也怪,狐狸洞竟塞得下一个大活人。回去后不久,蕙娘竟有了身孕。人们都说那是狐狸的孩子。”
“那么这孩子怎么样?生下来是人是狐?”也不知是谁插了一句。
“孩子?孩子自然是生下来了。和别家的也没什么差别,可毕竟是狐狸的小孩,留下来是祸害。于是……呵呵,于是村子里的人就将他献给了高丘神……”女子补充道,“所谓的献祭嘛,便是在五月初五端阳节,用五色长命缕将人牲捆绑在村口的神木上,并戴上礼冠,以求厌胜避灾。而礼冠,则是用五根桃木针钉入祭祀者的头颅,这就算作是给高丘神的祭品。”
“不对不对,你说的不对,这虽是高丘神的故事,但不是蕙娘的故事。你把两件事弄混了!”猎户着了急,语速不由加快了,“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。”
4那女子面有不悦,嗔道:“那你倒是说说看,你听到的故事。”
“我听村里的老人们说,那个蕙娘,是个身负恶煞的孤女。三十多年前,有对号称是避兵祸而至荆山的夫妇到了夔村,女的就是这个蕙娘了。因为村中高丘庙的老庙祝方巧死了,他们夫妻二人便住进了神庙。村民们虽对他们的身份有所怀疑,但由于蕙娘亲和友善,脸上时时带着令人亲近的笑意,对邻里们照顾得十分周到,又将神庙打理得井井有条,故而普受尊敬。可蕙娘的丈夫却不一样,他行为举止常常十分奇怪,即便是寒冷的冬天,也穿着轻薄宽大的旧衣,有事甚至会口发狂言,赤膊跣奔。蕙娘夫妇到了夔村没多久,就生下个儿子,名叫阿蓬。自打孩子出生后,蕙娘的丈夫就很少回夔村了,据说是在山外又谋了个幕宾之职。”
猎户缓了口气,又继续讲:“有一年,蕙娘的丈夫回村后,性情变得更加喜怒无常,经常为一点小事打骂蕙娘和儿子。有一次,邻里听他家闹得凶了,就想要上门劝说,却无意中听到,阿蓬居然是蕙娘和别的男人的儿子!不仅如此,原来这蕙娘曾是建平太守的家妓!此事一经传开,村民们都议论纷纷,在夔村这种守旧的地方,贞洁被看得十分重要,像这种女人住进了神庙,简直是对神灵的不敬!可想而知,这一家子,从此在夔村遭受了多少冷眼和嫌恶。”
“后来呢?”一直聚精会神听故事的女子忍不住问。
“后来,我曾多次出面,不让那群同龄的孩子辱骂欺负阿蓬。”猎户拍了拍胸膛,有意说给那女子听。
女子嗤笑一声:“谁问你这?我是问你蕙娘一家后来怎样了。”
“咳咳,后来老人们都说,蕙娘是个不祥的女人,不然为什么她一来夔村,老庙祝就死了?同她相关的人只怕都会被她克死。果然,怪事屡屡发生,先是蕙娘的丈夫暴死在村口,接着阿蓬开始不断遭到鬼怪的袭击,据说那鬼以鸟的形状飞来,化为一团影子,意图夺取他的身体。再后来,阿蓬也失踪了,蕙娘日日夜夜在山中寻找她的儿子,直到有一天跌断了腿。夔村的村民怜她夫死子散,虽然畏惧她身上的恶煞,但多少也会帮衬一些。不过,在阿蓬失踪后,蕙娘身边再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,也许是她的儿子以祭品的身份换得了高丘神的宽恕吧。”
听完他的故事,一直未曾说话的青年忽然道:“你方才说建平太守府上的倡女?我倒是认识一个这样的女子。不过,不叫蕙娘,叫阿芷。”
“这位一看就是从州郡来的,我听说那些富贵人家都爱养家妓,过去我们村的蕙娘也是个美人,长得……你别说,还真有些像这位……”猎户说着,转过头,仔细打量了一遍那女子,突然住了嘴。
那个青年却冷笑一声:“纵有倾国之姿又如何,不过是玩物而已。阿芷的父兄可真不是东西,酗酒好赌,致使家徒四壁,便拿阿芷抵债。阿芷十三岁时被太守看中,蓄为家妓。太守同幕僚夜宴时常唤她作陪,她因见太守幕宾陈渭南风流倜傥,才学洽闻,遂对其青眼有加。一来二去,二人暗生情愫,但她深知自己在太守府中不过是一玩物,待年老色衰,必会被弃如敝履,倒不如早做打算,择贤而嫁。她看中陈渭南才华,知其虽为庶族,家境贫寒,做不得清官,但无论如何,总比在太守府中蹉跎一生强得多。于是常出资偷偷接济陈渭南,并将太守赏赐之物暗中换为银钱,终趁太守不在郡中之时,夜奔陈渭南。陈渭南虽垂涎阿芷美貌,却万不曾料想阿芷如此果敢。都说倡女声色最廉薄,怎的偏让他碰上个有傲骨的家妓。但陈渭南那时得此美人垂青,一时气血上涌,真将自己当成了风流才子,无双国士,便欲携阿芷私奔出荆州,至他处另立一番事业。哎,可惜可惜,阿芷本是个聪慧灵巧的女子,却跟了陈渭南那样一个金玉其外之人,真是天妒红颜。”
一直烂醉如泥的老者,不知什么时候坐直了身子。他说:“你,你们,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?”
众人安静下来,侧耳听去。
5窗外的雨声停了,风声也止了,屋子里的火依旧燃烧着,可房内四周却不知从何时开始,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
火变成了唯一的光源,所有人,包括一直呆在角落里的青年,都向着火堆移近。
霎时间,火焰猛地虚晃起来,将众人的影子晃得一阵颤栗,女人吓了一跳,失声惊叫。
她一叫,引得所有人都心悸起来。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好像有人在哭泣。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有人在屋内哭泣。
哭声像是长了翅膀,从左飘浮到右,从东游移至西。
“什么人在哭?”老人颤颤巍巍地问。
猎户的脸色很不好看,他用一种几近恐惧的语调回答:“这是……楚魂鸟的叫声。”
龙景云大惊失色。他知道,每当这种鸟出现,就一定会有人死去。与此同时,他的头痛得更厉害了,好似有跟钢针扎入了脑颅,每吸一口气,都连带着痛不欲生的苦楚。
“楚魂鸟,楚魂鸟……过去每当楚魂鸟出现,村子里就会有人死去。”猎户惊惧地扫视所有人,“楚魂鸟会带走我们其中一人!”
悲凉的哭泣声又传来,并由低沉转为凄厉。
龙景云双脚一软,瘫坐在地,他的呼吸也变得紊乱。
“真可怕。”女子尖声道,“我听说,楚魂鸟是楚怀王之魂所化,怀王被骗入秦,客死异乡,故而他死后,最恨的,也就是说谎的人。”
猎户的声音也有些发紧:“是有这种说法,楚魂鸟会带走说谎的人……”
唯有那个去往建平郡的青年冷哼一声,轻蔑地看向猎户:“什么楚魂鸟,子不语怪力乱神,都是自欺欺人罢了。”
说完,他站起身,背对着众人,朝着方才“门”的地方摸索过去。他两只手朝前探,突然间动作就停住了。
他的脸色变了,两眼发直,双手好像触到什么般弹了回来,随之发出声凄厉的尖叫,对着黑暗中的某一处呼号:“冤有头,债有主,不是我害的你……”
众人望着面前的沌暗,又惊又怕,却又看不到任何东西。他们越挨越近,恨不能抱成一团。
看不见的怪物像是逼近了青年,他脚步紊乱地连连后退,足下一个打滑,一头跌倒在篝火旁。飞扬的火星燎烧过他的鬓角,将发丝烧的焦黑一片,而他仍是直勾勾地望着某种不可捉摸的事物:“我错了,是我错了。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。我是爱慕阿芷,所以当得知她同你私奔时,我嫉恨得发疯。明明我什么都不比你差,为什么那女人偏偏选你!我没想到,几年后还会在南郡遇上你,我嫉妒你们二人能够相伴终生,嫉妒你做到了我不敢做的事情。所以我才会说,阿芷的孩子是太守的……可我没想到……人之多言,亦可畏也……”
众人见他情绪失控,也跟着惊慌失措,纷纷站起身,寻路逃命。
神庙原本就很小,可他们的手怎么都摸不到墙。他们颓丧地退到篝火旁,明暗不定的火焰将人心无休止地动摇,一张张脸上黑白不明。
女子“哇”得一声坐在地上哭起来。她的哭声和青年断断续续又疯疯癫癫的自叙杂糅在一起,听得人心乱如麻。
“我我我,我说!我说!”那老头的酒彻底醒了,连滚带爬地抢着说话,脸上的皱纹与五官扭在一起,滑稽又怪异,“是我把二丫卖了,我对不起她,我对不起她,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我和儿子总不能等死……我知道错了,我知道错了……”
说完,他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朝着某个辨别不出的方向“咚咚”磕头。
可阴影并没有因此而减退。
“我……我也说实话。”猎户额头冒汗,手脚却冷得发麻,“我从没制止过别的孩子欺负阿蓬……我其实是带头的那个,我骂过他‘野种’,还打过他。可是,可是,那都是过去的事了,我那时还是个孩子……”
荒沌的陋室里乱做一团,每个人都自顾自地说着忏悔的话,可哭声却随着混乱越来越响,最后甚至变成了一声声与众人的恐惧难舍难分的哀嚎,像一根根尖锐的钉子,扎入了脑髓。
“还有谁?还有谁没说真话?”猎户捂住耳朵,悲惧地问。
猛然间,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龙景云和小谢身上。
小谢仍是举重若轻地笑着:“我什么都没说过,又何谈真假?不过——”
他转脸望向龙景云:“龙兄,我记得你在路上也讲过蕙娘的故事,虽只讲了一半,不过你讲的可是真的?”
可这时的龙景云却抱着头,痛苦地扭作一团。
他紧紧闭住双眼,将自己封闭在空无一物的黑暗中,可黑暗像是死寂的水面,突然间产生了细密的漪轮,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其间浮起,又好像有什么要冲破他的脑颅,置他于死地。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凄厉的哭声即便在他堵住耳朵时,依然穿入脑际——它来索命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,躲不开,忘不掉,它还是时时出现在最幽暗的梦境里。它没有脸,没有形状,它是一团像鸟又像人的影子,它意图占据他的身体。
龙景云想要活下去,就像那些年,那些被五色缕缠绕着的夏天,那些女人们发自内心的嫉恨与孩子们少不经事的嫌恨交杂在一起,让人不寒而栗。
可他依旧要活下去。
现在,他蜷缩在地面,潮湿泥土的气息钻入鼻腔,令他有些微微失神,那种熟悉的泥土气迥异于他处,在他的头又开始疼痛时,他突然意识到,那是燃烧的艾草与缩酒白茅,是残破的草席和陈旧的宅舍,甚至还有,还有浆洗得发了白,褪了色的粗麻衣衫的味道。
那其实是……
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。脑海中破碎的片段变得越发混乱失序。
6该从哪里开始?谁真谁假,孰是孰非?
他必须活下去,这么多年的挣扎不能付诸东流。脑际中偶有一处白光闪烁,他惊梦般睁眼,看见所有人围绕着他。
那个老人似乎在叹息着,点钱的手却一刻不停:“家道艰辛,我这么做也是万不得已。”
那个青年半是嘲讽,半是冷笑地望着他:“太守如此震怒,四处追查你们的下落,难道只是为了区区一个家妓?当然不是,太守是为了阿芷肚子里的孩子。”
那个猎户好似在指着他,狂妄又恶狠狠地说:“倡妓养的野种,你爹替别人养儿子,还被你娘被克死。你早晚也会被克死的。”
但他们又好像什么都没做,什么也没说,只是那样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半疯的他。
龙景云头疼得近乎麻木,直到那女人走到他身边,轻轻扯住他的腕子,在上面系上一条长命缕。
“这些天你总睡不好,熬过五月五兴许就会好些。”女人说话的腔调永远都是柔柔的,却对他一身伤痕与污浊显得无可奈何。
他最终定定地望着那女人,望着她身后站着的,一个孤零零的影子。
那个黑影越来越近,它越过了鬻卖亲女的老人,越过了搬弄是非的男人,越过了欺凌弱小的猎户,越过了女人,越过了小谢,它在一片死寂中第一次露出了脸。
“别……别过来!别过来!”龙景云蜷抱着剧痛的头颅发出痛苦的呜咽,身上的破衫被汗水浸透,身体止不住地抽搐。
他看清了,那个始终不肯放过他的黑影是个双眼赤红的男人,他步步逼来,一只手中紧握着铁锤,另一只里则是尖锐的桃木钉。
“爹……”自龙景云打颤的牙齿间,挤碰出了连他自己都听不清的呼喊。
然而男人仿佛听清了,他怒目圆睁,抡起手,长长的木钉擦过龙景云的脸,留下火辣辣的痛。
“野种!”男人低声咆哮着,将长木钉举过龙景云的头顶,而握着铁锤的那只手,就势砸下!
桃木针刺入头颅,龙景云悲苦地哀嚎回荡在雨夜的荒山中。他抱头翻滚在地上,满地的泥污将他身上上好的衣料染得浊黑不堪,让他一度焕发光彩的生命再度低到尘埃里。
随着那根尖针入脑,影子遁迹。那些熟悉的味道不断冲入鼻腔,令他不得不记起,那其实是某个女人的气息。
那个女人不是什么富户家的女儿,她是个被家人当作物品买卖的倡女,是村民们议论和嘲讽的谈资。
她是蕙娘,也是阿芷,甚至是卖女老人口中的二丫。
她是他的娘亲。
三十年中,他不断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,试图让自己的愧疚变得更轻一些。毕竟,离开一个身负恶煞的女人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?毕竟,这样母亲让他蒙羞,他只想要一个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的母亲。
“记得吗?‘杀死’你父亲的不是你母亲,而是你。”那个容貌肖似母亲的女子伏在他身边,好似一个对着生人耳背吹气的鬼。
“我没有!不是我!”龙景云涕泪横流的脸上,还剩下坚守底线的最后一丝强硬。
“哎——”女人长喟,“为什么人类总喜欢掩盖真相?每个人都为了相同的目的说谎,每个人都刻意隐去了自己的罪孽。可是——真相同恶灵一样,总有一天会找到你。”
她站起身,俯视着龙景云,眼神冷锐又悲悯:“你做了那么多年的商人,如今想必已知道,五石散不能和冷酒一起吃。”
龙景云盯住她,仿佛能从她的眼神、她所说的字字句句中找回他丢弃了的事实。
“虽只是无心之举,但毕竟是你,结果了他的性命。那日,你因为被村中的顽童纠缠,回到家时忘了替父亲温酒,等到你父亲回来时,因五石散药力发作,再加上流言蜚语积日累月的烦扰,他早已对你动了杀意。于是他用桃木钉钉入你的头顶。”那女人张开五指,在他头顶细细摸索,“它好像还在这里呢。长久以来,它扰乱了你的记忆,抹去了此前父亲留给你的回忆,让那个本就不相亲洽的父亲化为这些年来如影随形的恶灵。”
她的指尖突然停在某个位置:“而你,却误以为是蕙娘克死了你父亲,并在自己创造出的‘恶煞’的侵扰下,认为下一个要死的就是你。所以……”
“别说了,求你别说了!”龙景云疯狂地摇起头,企图躲开女人的手指。
“呵呵……”那女人笑起来,她的手指仍是一动不动地停在他的颅顶,“身负恶煞的不是蕙娘,而是你啊。三十年了,阿蓬,每当恶煞出现时,其实是你在思念自己的母亲吧。”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龙景云失声地干号起来,他猛烈捶打自己的头颅,而那女人的所言好似决堤的洪水,灌入脑中。
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。因为日积月累的惧怕,他丢下母亲,逃离了夔村,逃离了他自以为宿命的死亡。
然而,脱去龙景云的外壳,他依旧是那个淳朴的、善良的、名叫阿蓬的少年。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的温和、宽厚与坚强,是他从不曾遗弃的,或许这,就是母亲陪伴他的另一种方式,可是这,又如何能弥补他对母亲的愧欠?
只有那年端阳节前,母亲系在他腕子上的长命缕,陪了他三十多年。依俗,长命缕该在端阳节当日丢入水中,以求消灾祛病。而他却时时戴着,哪怕褪了色,泛了白。那束五色丝,一直是他的心结,难以去除。
7“原谅我的私心,将你吓成这个样子。我这么做,为的是蕙娘的愿望。倘若不解开你的心结,无论于你还是于蕙娘,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。如你所见,我是栖居在高丘庙前神木上的死魂,时间久了,就被人们误认为是高丘神。你娘虔诚供奉我,我便报答于她。你一定疑惑,为什么我生着和你母亲一样的容貌?那是因为,过对于去的相貌,我已经记不得了。我先前所说的那个故事,是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娘在出嫁前被村里的长老玷污,长老编造了狐狸的故事,将自己所做的丑事掩盖下去。我娘在生下了我后羞愧自尽。十六岁那年,那个不顾伦常的恶心男人居然又妄图讨我做妾,我抵死不从,他便污蔑我是狐妖,将我活活钉死在神木上。哎,我和你一样,到现在,头还会痛呢。” 那女子自嘲似地一笑,笑容又甜美又悲哀,“人类啊,总把一切推到高丘神身上,什么高丘神震怒,高丘神索要贡品,最离谱的是高丘神娶新妇,哈哈,我本就是个女子,可怎么娶妻呢?一切都不过是他们为自己犯下的罪孽寻找借口而已。”
龙景云痴痴地听她讲完这一切。妖鬼尚且知恩图报,可他又拿什么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呢?
“多谢您。”女子回身向小谢行了一礼,“因我的私念,耽误了您的公事实在是抱歉。”
“不必客气,不过是顺路而已。”小谢摇了摇手,“更何况,我是个爱听故事的人。”
女子淡淡一笑,再度转向龙景云:“雨停了,阿蓬,该启程了。”
说罢,她的身形渐渐湮没在黑暗中,而老者、青年和猎户则变成了野鼠、狐狸和松鼠,同她一起消失了。
“来吧,龙兄,我送你最后一程。”小谢微笑着击了两下掌,黑暗退却,眼前依旧是萧索轮囷的神庙,却有天光照入。
神祠里照旧悬挂着长长短短的五色缕,那颜色也像这破败的屋子一样透着污浊。
而龙景云只是望向一个蜷缩在肮脏角落中沉眠的老妇。
他不知道,母亲这些年来是怎样度过的。村民的冷眼和唾弃,即便是现在想起来,也让他心有余悸。
现在,他那曾经美丽的母亲,也变得如同朽木一般,褶皱的皮肤裹着一副瘦骨,枯槁、憔悴,毫无生气。
到底是什么力量,让她坚定不移?
她不顾一切,放弃尊严地活下来,活下来是为了谁?
摔断了腿,一辈子都再没能走出过荆山的母亲啊,她所能想到的,做到的,唯一可以与儿子重逢的方式,就只有等待。
龙景云都明白了,他感激地回过头,看到牛车旁的白衣少年,也正微笑着看他。
你相信招魂吗?生魂也好,死灵也好,只有最纯粹的思念,能让魂魄归来。
“不必谢我。也不必谢高丘神。”名为小谢的少年道,“真正想让你回来的,是你母亲的思念。如今,前缘已尽,便可前往奈何桥畔,轮回往生。”
无可留恋。人世间最痛苦的,莫过于死别。
然而比死别更痛苦的,是覆水难收的悔恨。
龙景云握住老母干枯的手,睡梦中的老妪也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,收紧了五指,虽然那里什么都没有。
只要活着,就什么都有希望。可是,倘若死了呢?
“寿夭祸福,每每看到这些却无动于衷的司命,该有颗怎样的心啊?”小谢倚着牛车,自言自语,“人类那么善于后悔,而我至少还有替他们弥补心愿的机会,这样也算不错。”
“哼。唯有你做事拖拖拉拉,还喜欢沾沾自喜。”小谢正说着,却见一名黑衣少女骑着乌黑的高头大马,冷冷冲他道,“还不快拿着阴阳符回去复命。”
小谢低头看了看手中,一束五色缕躺在掌心,他淡淡一笑,翻身上了牛车,同那黑衣少女一道消失在暮色里。
不会有活人知道这对少年男女是谁。
也不会有人知道小谢生前的名字,他叫谢必安。
“有人说人在死前,会将生时经历过的事情一一忆起。还有人说,濒死时记起的是心中最深的挂念。”武罗一口气讲完整个故事,“咕咚咕咚”喝了两口水,又接着说:“荆山塌方之处,人们在被挖出的尸体中,发现有一具最奇怪。凭着他随身的印信尚能分辨出他的身份,他是江陵大商户龙家的赘婿。说他奇怪,是因为他脸上竟没有一点恐惧,相反,他是微笑着的,就好像得到了极大的解脱一般。”
我问武罗:“那蕙娘后来怎样了?”
“不知道。”
这算什么回答啊?我刚想抱怨,却听阿姐道:“好了子夜,轮到你了。”